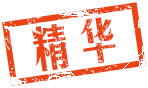|
|
本帖最后由 九文 于 2024-12-26 14:46 编辑
七律系列·19·陆游修行话参禅·一东
文/九文-2024-12-26-13:00-作于南京一中
死去原知万物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。
王师北定中原日?赵构南迁华夏宫!
怎悯情怀家国事?谁修乡土佛门风?
鸿书托付忧心绪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
陆游在其《老学庵笔记》中,曾有亲眼看见吴越王钱椒的长紫袍存放在华严禅寺的一段轶闻记述。
陆游所处的年代,是北宋和南宋更迭的特殊历史时期,兵连祸接,内忧外患……当局荒谬乖张,社会动荡诡谲,官场险恶黑暗。他在宁德只做了四年的主簿小官,后改授敕令所删定官,于1161年罢归乡里,1163年替张浚策划北伐失败,又被免去官职。过了七年之后,1170年,陆游才到四川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任通判,又到宣抚使王炎的幕府中**军务。王炎被调回朝廷,幕府被撒散,陆游调到成都任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的参议官。
由于陆游绍兴家族前辈笃信佛教,使他从小就受到佛教思想的薰陶,因此,在他的诗作中,有不少篇章与佛教有关。如专程赴普陀山和支提山朝圣、礼佛、写诗等事例。他即使在随军,或在幕府任上的时候,也总要到附近的寺院礼佛、写诗,甚至借宿于简陋的寺舍,从不计较居住条件。他相信因果,喜素食,行动不拘礼法,被人讥其颓放,因自号放翁。他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较深,不与当时的强权者同流合污。陆游在川陕生活了九个年头后东归,即在江西抚州今江西临川、浙江严州建德县、临安杭州等地只做了几任地方小官,于1189年底又被罢斥了。从此之后,直至1210年这段晚年生活,都在故乡中度过,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,同时经常上寺院,与僧人成了莫逆之交。其密切的关系,正如他诗句中描绘的:“共话不知红烛短,对床空叹白云深”。
嘉定元年1208九月,陆游以八十四岁高龄,应宁波天童寺住持无用禅师弟子之请,为《无用禅师语录》写序。天童无用禅师1138—1207,法名净全,诸暨人,俗姓翁,弱冠出家,后入径山参大意宗呆,得授心印。陆游的《序文》是:
伏羲一画,发天地之秘;迦叶一笑,尽先佛之传;净名一默,曾点一唯,丁一牛刀,扁一车轮,临济一喝,德山一棒,妙喜一竹篦子,皆同此关捩,但恨欠人承当。
天童无用禅师,盖卓尔能承当者。末见妙喜,大事已毕,岂有住山示众之语可累编简哉I放翁谓:“若不投之水火,无有是处。”惟韩退之所云“火其书”,其语差似痛快。又恐退之亦止是说得耳!五百年后,此话大行,方知无用与放翁却是同参。
《序文》首先列举“伏羲画八卦”、“迦叶一笑”等几个典故,以历史上儒家、佛教界名流和良工巧匠在参修、行事、传道中掌握“关捩”以川页利解决事物矛盾和启发他人警觉的例子,解释、说明“关捩”的重要。譬如唐代高僧义玄?—867住真定临济院创临济宗,常用叱喝之声提撕弟子警醒,称为临济一喝。还有宣鉴禅师782—865初住德山,其道峻险,棒杀天下衲子,称为“德山一棒”o棒与喝均为提撕弟子惊醒之法,有“一喝大地震动,一棒须弥粉碎”之说。因为拨动“关捩”而顿然感悟的,更是屡见不鲜。这说明“关捩”无所不在,要在拨动与启发。
禅宗的“棒、喝”是拨动“关捩”的有力工具,但如果“关捩”结构尚未完善,那么,即使棒如雨下,喝声震天,也是无济于事的。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,外因是变化的条件。
而《无用禅师语录》正可作为承担拨动“关捩”作用的外因。那么,陆游却说:《语录》无需编简,可投之水火,为什么呢?正如物乙经》所云: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。陆游的一生不是一帆顺的,由于他经历了坎坷的遭遇,亲身受到苦难,深刻体会到老百姓的忧患疾苦,故而他的诗作,富有浓厚的悲悯情怀。再者,他平生崇佛,对佛理多有研究,所到之处,多住在寺院,广泛结识佛门僧侣,从而言行、诗作中蕴涵着深刻的佛家思想。再阅其《语录》序一文,所举的实例,及措词、内容,可窥出陆翁学佛,已深得三昧的境界。文章的结尾,又明确地表示:“无用与放翁却是同参。”同参指的是共同参禅实践,而且两人的悟解也是一致的。
从以上的事实,特别是在公元1189年,最后一次被罢斥后,看出陆翁返回老家,过晚年生活的时期,更贴近了佛门,学佛也就更精进了。
公元1210年春,陆游八十六岁,与世长辞,临终遗诗《示儿》:
死去原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。
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
这首绝命诗的精神与佛教报四恩中的报国土恩是一致的。他临死前,心中念念不忘的,不是求自己个人的生死,而是祈求祖国领土统一完整,人民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,体现出诗人高尚的思想境界,不愧为一位杰出的人民诗人。
|
|